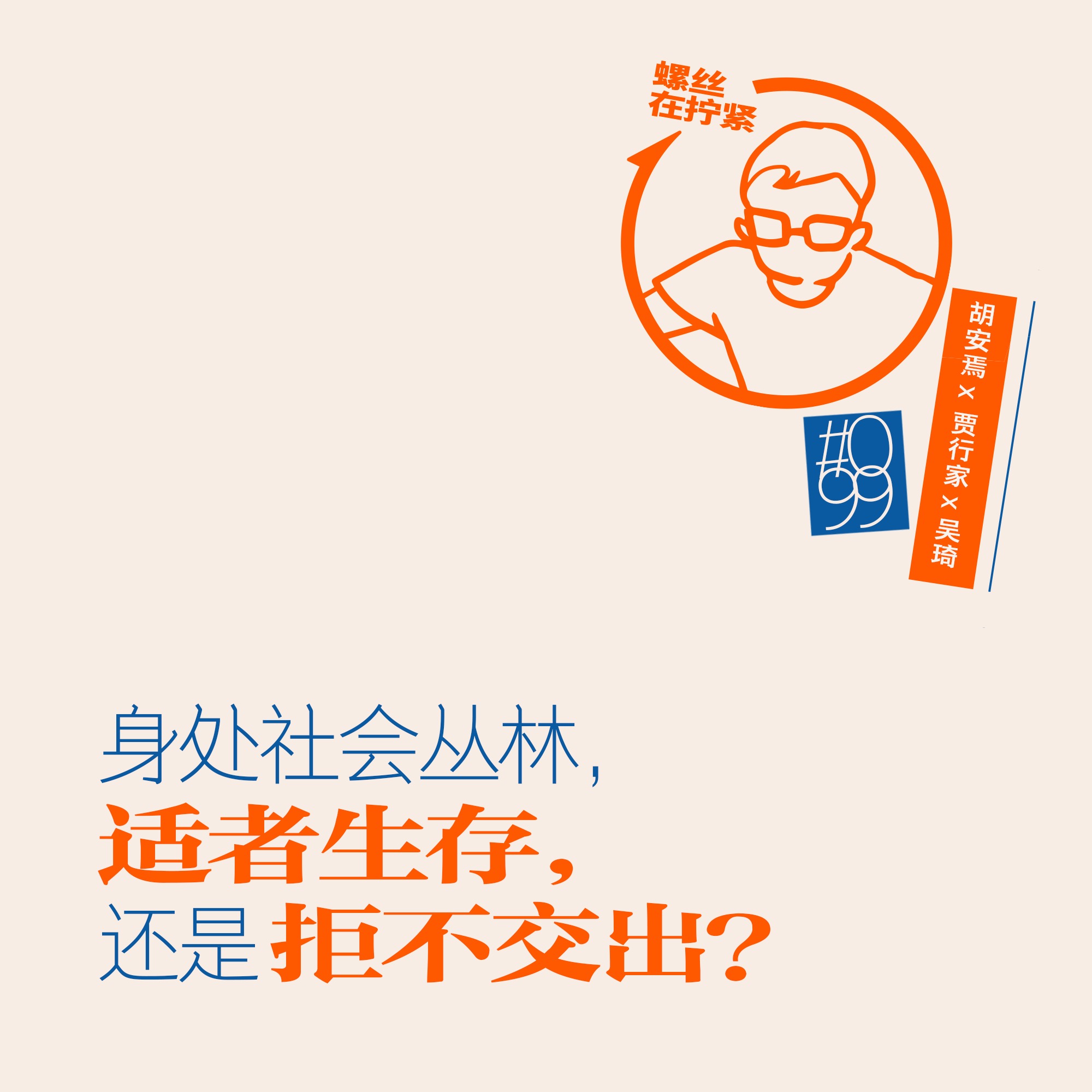
在《生活在低处》里,胡安焉写下了自己在南方开女装店时,与一位有精神问题的女顾客的会面。她走进他的店面,没有进入试衣间,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接连套上了三条牛仔短裤。
“我的眼睛也湿了,眼泪随时要夺眶而出……”他写道,“从她的脸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她就是另一个我——惊慌,恐惧,孤独,委屈,被人不怀好意地围观,腿上还挂着三条牛仔短裤——只不过我还有力气遮掩,她却只能就这么袒露出来……”
这个故事,以及他在这期节目开头分享的另一个故事,促使胡安焉反思有意义的生活应当追求些什么。写作和阅读会是答案吗?还是通向答案的许多条路之中,容易被误认为答案的那一条?
这是贯穿本期「螺丝在拧紧」与「大望局」的串台节目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隐隐地探向生活的“低处”——也可以说是“深处”:在恶意四涌的环境里,你要在多大程度上“适者生存”,多大程度上“拒不交出”?你如何面对自己偶然暴露的、连自己也不知道的一面?柔弱真的与智慧相伴而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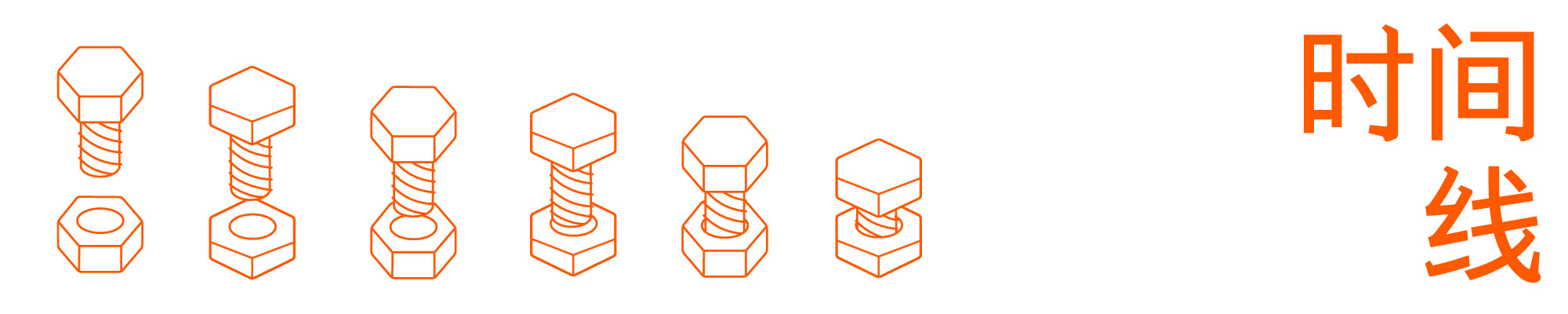
01:17 自我介绍之前,先各讲一个故事——
胡安焉:在医院门前,处于“特殊状态”的两位妇女
吴琦:那个买水果的大姐,成了有名的“鸭腿阿姨”
07:51 只要把头低下,总有人比你的处境更艰难
20:14 在南方开女装店,“你必须要学会口腹蜜剑”
31:18《我在北京送快递》总被误以为是一个“喜欢文学的快递员”的故事
33:56 三个“天问”:
你们正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认为生活是什么?
39:56 胡安焉:真正“低物欲”的人,不会有“低物欲”的概念
43:11 吴琦:所谓“社会化”的过程,根本没有帮助你克服恐惧,反而不断为恐惧增加新的内容
49:13 贾行家:隐居生活的困难,在于斩断被别人需要的需要
59:51“仿佛这一生是偷来的、赚来的,所以当中经历的所有痛苦和欢乐,都是不应得但得到的东西”
1:04:40 你是否曾暴露出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一面?
1:08:50“很多人因为无法面对自己的肮脏,才不停地讴歌母亲”
1:10:44 阅读与写作,对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1:25:39 最后,去读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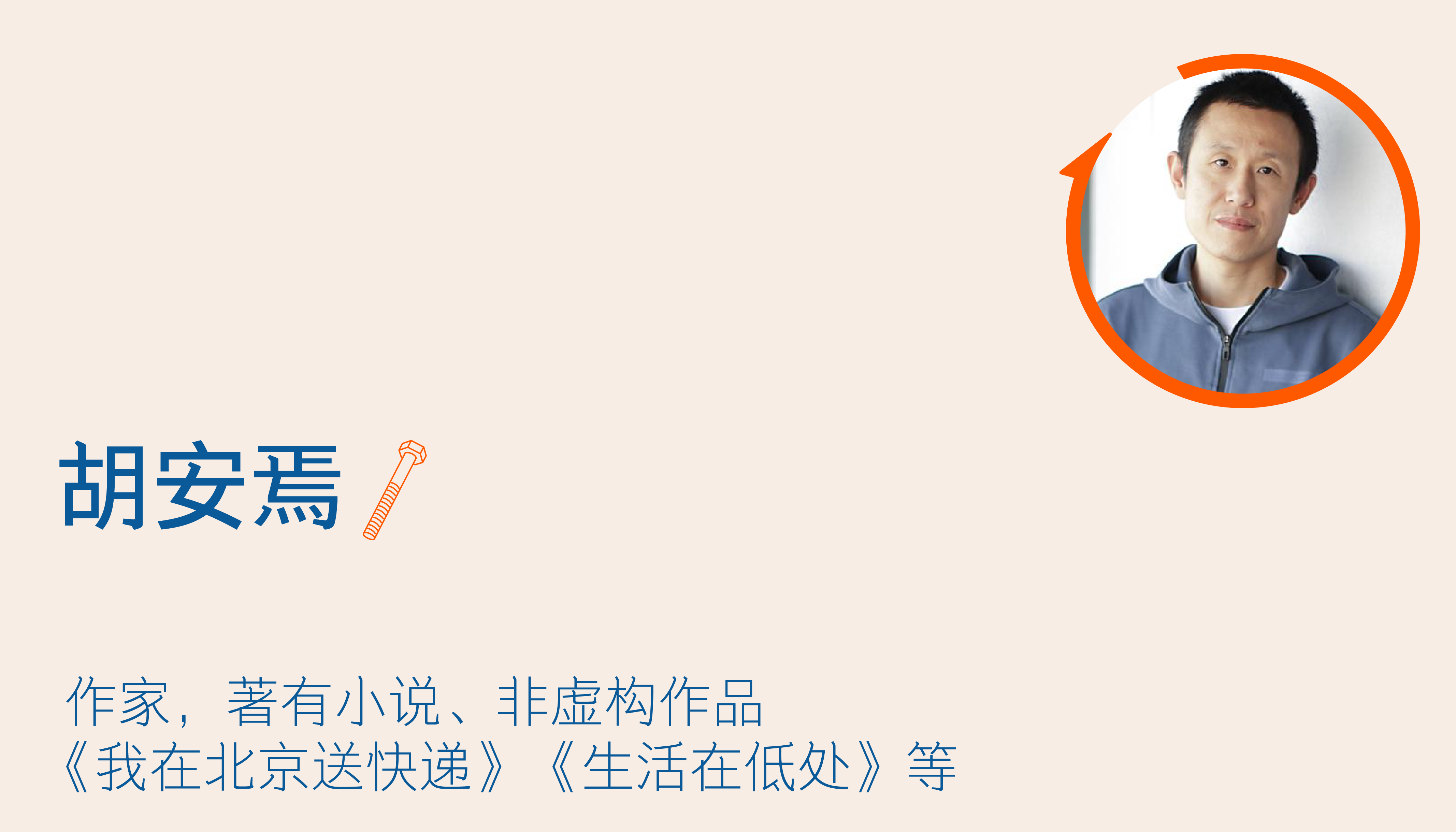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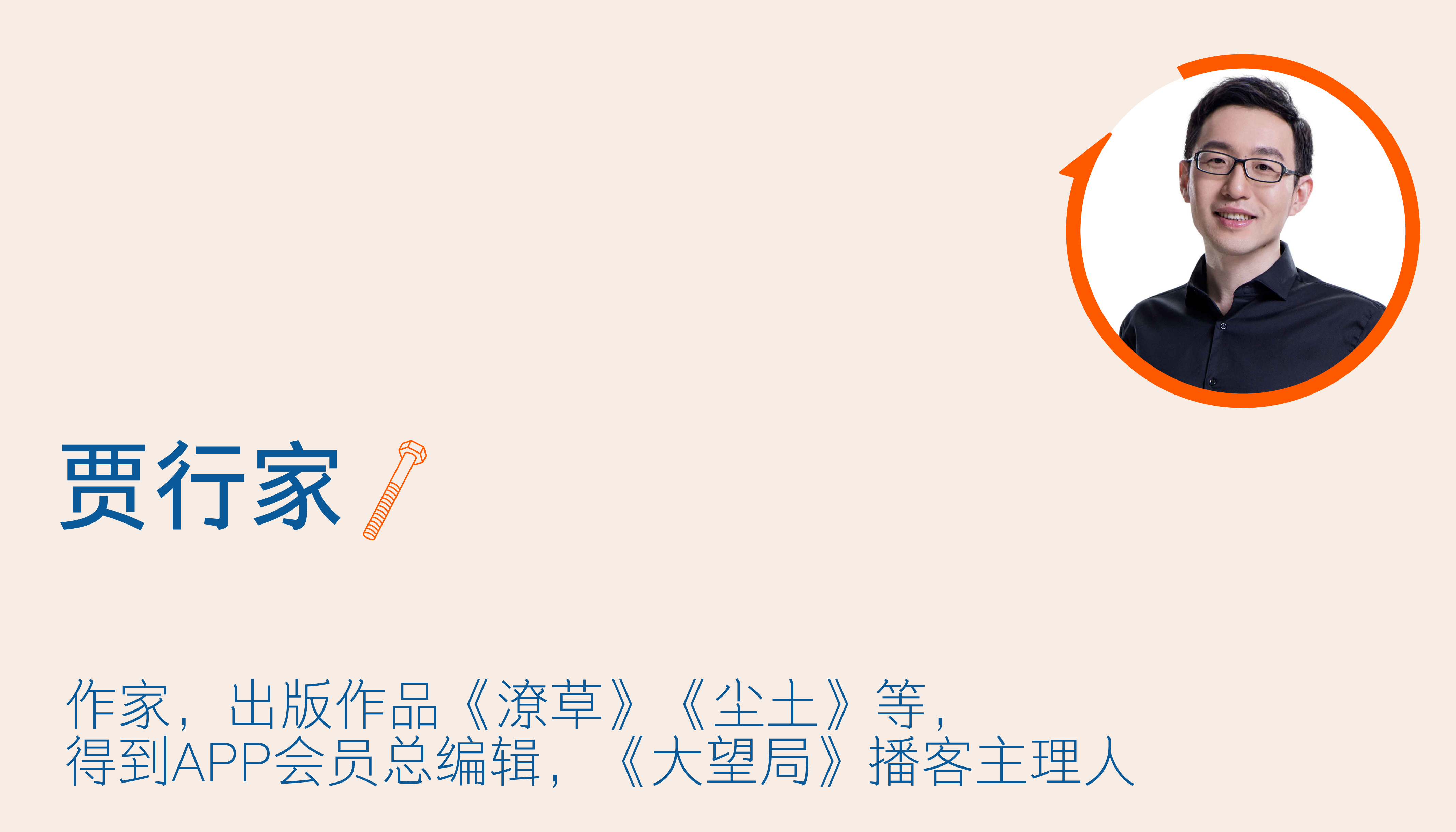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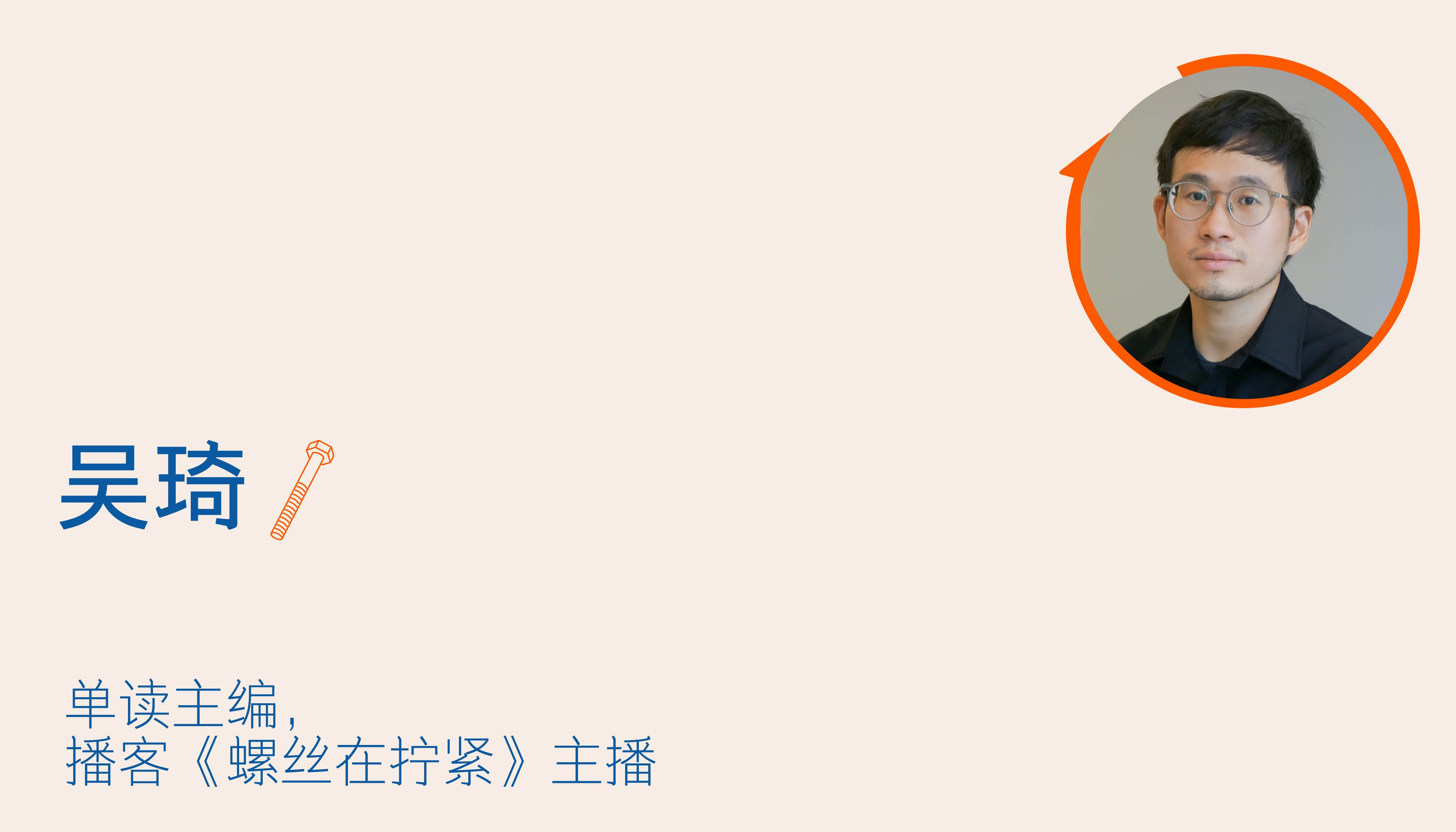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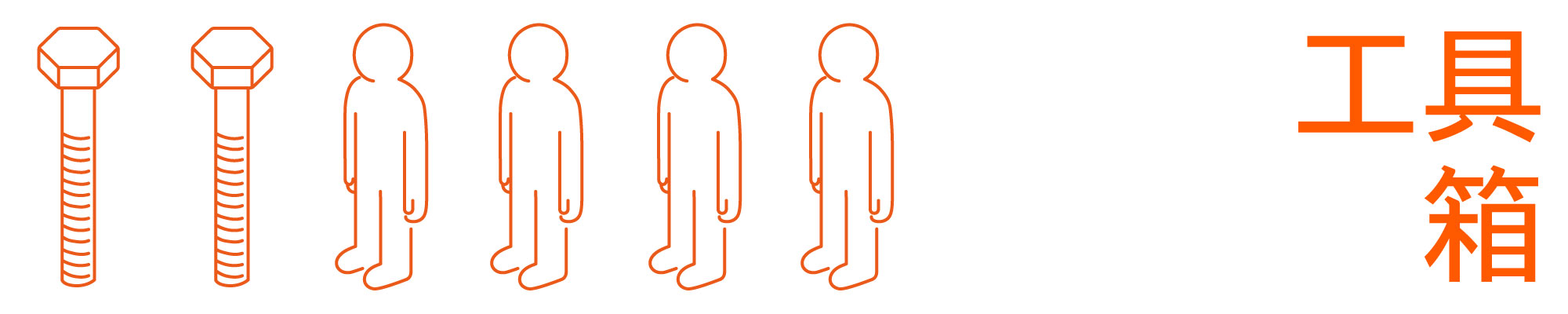
|工具箱|
-谈话中提到的书籍
《生活在低处》,胡安焉著
《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著
《一件小小的好事》,[美]雷蒙德·卡佛著
《麦田里的守望者》,[美] J. D. 塞林格著
《九故事》,[美] J. D. 塞林格著
《人,岁月,生活》,[苏联]爱伦堡著
《悲伤与理智》,[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著
《词与物》,[法]米歇尔·福柯著
《我不想保持正确:拉图尔对塞尔的五次访谈》,[法] 米歇尔·塞尔 、[法] 布鲁诺·拉图尔著
《把自己作为方法》,项飙、吴琦著
《篮球飞人》,[日]井上雄彥
-谈话中提到的电影
《里斯本丸沉没》(2024),导演:方励
|互动方式|
如果你对本期话题或本节目有任何想法或问题,请大胆在各收听平台评论区留言,或者微博吴琦@五七与主播互动。
|本期音乐|
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Today, Tom Odell
|本期封面|
摄影:吴琦
|鸣谢|
大望局播客(制作人:温蒂)
|关于「螺丝在拧紧」|
监制:彭倩媛
制作人:胡亚萍
编辑:菜市场
剪辑:椋生
视觉设计:李政坷 欧梦婷
节目运营:刘雨萱
原创音乐:徐逍潇
实习生:李天漪




 39069
39069 178
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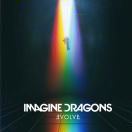












2. 对事物的准确记忆是写作者的一种天赋。
3. 尽管那些痛苦的经历已成往事,你仍应深入其中,用写作和阅读给它们建立一个说法。
4. 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理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接受它。你所接受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你的理想生活。
5. 选择隐居或独自生活的人,需要放下被社会需要的期望。
6. 可能真正的隐居是内心的隐居。这意味着我内心的一部分不再向别人敞开,甚至不交托于所谓的文学和书写,而是决定留给自己。
7. “历史始终在不知疲倦地败坏地理的名声。唯一的抵御方式就是成为一个流浪汉,一位游牧者,成为一道阴影,掠过倒映在水晶水面中的那些花边般、瓷器状的廊柱。”——《悲伤与理智》
8. 死于远方者,即为勇敢之死。
9. “对我来说,写作既是对生活的消化和体味,也是对自我的不断深入和辨认。生活、自我和写作这三者在我身上的关系大约是,首先生活和阅读提供了经验,我通过这些经验观照自身、澄清自我;而写作最初是我对这些观照和澄清的不同形式的投射,之后则成为一种从自我到无我的超脱——在人的生命尺度内,它不大可能完成,因此我的写作也不会终止。 ”——《生活在低处》
10. “我也不是个目标清晰、意志坚定的人。假如今天我写下的这些让人觉得比较清晰和坚定,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堆叠把其中的褶皱都压成了实心。”——《生活在低处》
11. 也许,智慧是和柔弱相伴而行的。
12. 我们常误以为人生目标是站在人生之外去选择的,就像点菜一样选择要过哪种生活。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都是被抛入生活中的,遇上什么就是什么。
13. 只生活一次是不够的,那些生活还需要在文学里“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