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雷恩,欢迎收听本期浅尝。
今天想要聊一本诗集,就是香港作家也斯的《雷声与蝉鸣》。
如果你平时没有读诗的习惯,那正好,我也没有。
诗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地方,我对诗的理解基本停留在小学课本阶段,一首诗一旦不押韵,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尤其对于现代诗,一下子没了格律,好像突然变得谁都能写,写出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再使劲换行就行了。
好在我还没那么虚无主义,把现代诗整个判死刑,对于真正的诗人,始终保持着敬意,至于谁算是真正的诗人,由于自己缺乏判断的能力,只能诉诸于公论,也隔三岔五的尝试去阅读那些公认优秀的作品,只不过通常还是get不到这些诗好在哪。
尤其是外国诗,一经翻译,就更复杂了,觉得不知所云时,就搞不清到底是我的问题、诗的问题还是翻译的问题。
不过,偶尔,还是有诗句能够打中我,让我觉得语言的美,在诗中才能得到最恰当的体现,当然这些通常都是广为人知的诗句,可以说是现代诗中的爆款,例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或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北岛一篇散文中的几句也广为流传,“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 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总之,当一首好诗传到我耳朵里时,通常这首诗已经传遍半个互联网了。
但今天要聊的这本《雷声与蝉鸣》不同,这里没有爆款,也不是网红,当然对于真正的诗歌爱好者来说,这本诗集绝对不是小众,作者也斯更是香港文坛的泰斗级人物,只不过对于我这种诗歌的路人粉,找到这本诗集的确有种捡到宝的喜悦,自然也就想分享出来。
先是偶然看到一些诗句,然后找到了整首诗,最后找到了收录这首诗的诗集,就是这本《雷声与蝉鸣》。
最先发现的诗叫作《中午在鲗鱼涌》,鲗鱼涌是香港的一处地名,普通话读起来很奇怪,但粤语我又不会读,所以私下里我把它叫作摸鱼之歌,我先来读一部分
有时工作使我疲倦
中午便到外面的路上走走
…
在篮球场
有人跃起投一个球
一辆汽车响着喇叭驶过去
有时我走到码头看海
学习坚硬如一个铁锚
有时那里有船
有时那是风暴
海上只剩下白头的浪
…
有时我在拱门停下来
以为听见有人唤我
有时抬头看一憧灰黄的建筑物
有时那是天空
有时工作使我疲倦
有时那只是情绪
有时走过路上
细看一个磨剪刀的老人
有时只是双脚摆动
像一把生锈的剪刀
下雨的日子淋一段路
有时希望遇见一把伞
有时只是
继续淋下去
烟突冒烟
婴儿啼哭
路边的纸屑随雨水冲下沟渠
总有修了太久的路
荒置的地盘
有时生锈的铁枝间有昆虫爬行
有时水潭里有云
走过杂货店买一枝画图笔
颜料铺里永远有一千罐不同的颜色
密封或者等待打开
有时我走到山边看石
学习像石一般坚硬
生活是连绵的敲凿
太多阻挡
太多粉碎
而我总是一块不称职的石
有时想软化
有时奢想飞翔
这首诗写于一九七四年六月,当时作者25岁,正是一个不想上班的上班族,我非常能理解这种心情,读这首诗时几乎能够想象当时的情景,趁着午休的一小时逃离格子间、写字楼,走在街上,一路走一路看,恨不得把外面的世界都装到眼睛里,好在下午回到工位后能时时浏览,让自己挺到下班时间。
这么多有时,这么丰富的细节,显然这不是一天的经历,八成是一有机会就要下楼走走。
喜欢这首诗大概就是由于这份同为打工人的共鸣,虽然相隔四十余年。
从诗中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疏离,一种与城市与标准化的格格不入,社会告诉你你是块石头,但你发现自己有时想软化,有时想飞翔,这种感受贯穿整本诗集。
例如另一首诗《抽奖》
他得到一套北欧家私
他得到一个耳塞
…
他得到两个富有的姑婆
和一头鹦鹉
…
他得到一只不断上升的股票
一所不断下沉的大厦
只有我
仍然两手空空
每次仰望
就仿佛听见
有人在远处发笑
…
在错误的火车站
等候下一班车
在高速公路上
做一匹马
…
人们捧着抽到的东西
赶着跑去把奖品收藏
我扔在这里
慢慢地走
再会了先生
再会了
女士
我在后面叫
再会了
南瓜和玉蜀黍
捧着这么多东西走路
小心不要摔倒
但他们以为我要赶上去
却都跑得更快了
把人生比作抽奖,每个人都紧紧攥住自己抽到的东西,并时刻提防着有人赶上来,有些可笑有些可怜,但现实就是如此,如果可能,谁不想抽到更好些的人生呢。
而作者却像一个局外人,一个不属于这里的人,和那个从写字楼逃到街上的石头一样,在错误的车站,等下一班车,在高速公路上,做一匹马。
他想提醒那些跑的太快的人,拿这么多东西小心摔倒,但人们却以为他在追赶,都跑得更快了。
在高速公路上,做一匹马,对我来说这样的意象就是诗的魅力,一下子就把某种久久徘徊的情绪凝聚成了一幅画面。
一个背离时代的人,但与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辆相比,马才是有生命的存在。
前几期节目聊过一部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里面也有大量类似的对照,徒步者与司机、拉萨与百威、藏服与皮衣。
上周末又看了一部万玛才旦导演的作品《气球》,影片开头的一段对话,就让我想起了这首诗,那段对话大概是这样的,老人问儿子你这摩托车骑了好几年了吧,儿子说五年多了,毛病也挺多,老人说,现在都骑这个,怎么可能比马好呢?儿子说,是啊,都把马卖了换摩托了,现在哪有什么马呀,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但总有些人并不想跟随,无力抵抗,就变成了诗,做一匹在高速公里上奔跑的马。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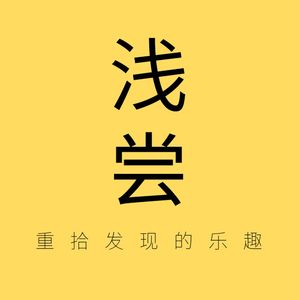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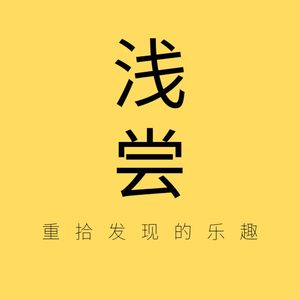

 26
26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