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刷到一个帖子,博主说自己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究竟从哪一步开始走错了。在学校努力读书考进班级前列、学校前列、全省前列,到了大学后卷社团卷实习卷绩点,给导师干活写论文,在激烈地竞争中面试企业,入职后又在更激烈的晋升中抢夺职位,讨好领导,完成越来越重的指标。如今,看不到晋升的希望,身边朋友也越来越少,恋爱只能靠相亲来认识异性,又总也不满意,自己的人生究竟是哪一步开始走错了呢?
评论区有人说,问题出在博主一直在社会设定好的规则里做正确的事。任何一个社会都期许10-20岁的学生安心学习,20-30岁努力工作尽快成家,30-40岁则养育好子女。社会默认了想要晋升就得耐心等待机缘,真有机缘了又要把机会让给年轻人。社会期许每个人都循规蹈矩,这有利于社会的平稳运行。
这种期许,要求人们都参与草台班子演戏。倘若不参与,置身事外,就变成了一个“局外人”,在外人眼里变成了一种清高、一种格格不入的异常。
这就是今天介绍的法国作家加缪的第一本书《局外人》,他描绘了这样一个角色:主角默尔索对一切都兴致缺缺,母亲去世他也并不悲伤,第二天就和女友约会去了。他对爱情并不在意,当女友问他是否爱自己时,他也明确表示自己不。工作上领导给予他外派的机会,满心以为默尔索会感激涕零,但他却“悉听尊便”。“无所谓”“不知道”是他的口头禅。
他因防卫过当杀人,上了法庭。律师认为他罪不至死,但法官得知默尔索竟对自己母亲去世不感到难过,由此判定他是个罪大恶极的人,必须处以死刑。面对死刑,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淡然。行刑前,一位神父拜访了他的牢房,表示只要他愿意忏悔,愿意皈依天主,就能免除死刑。他表示自己没什么可忏悔的。神父相当惊讶,他疑惑所有人到了这一步都会忏悔的,为什么你会不忏悔呢?神父苦口婆心地劝他忏悔,为他讲解信仰天主的种种好处,他就是不信,并在最后忍无可忍地揍了神父,坦然迎接死刑。
对于默尔索,我们不去评价他做的对与错,任何的评判都是建立在我们读者个人的经验和社会默许的道德习俗上才能成立的。抛开一切,我们应该承认一个独立的人,应当有决定自己是否悲伤的权利、具有保卫自己而使用武器的权利、以及选择去死的权利。
然而书中上司索取下属的感恩戴德、法官的大义凛然、神父的狂热盲目,都构成了一幅幅荒诞的景象。从这里开始,加缪完成了他的荒诞三部曲:《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
加缪说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对此我也深有同感。俄乌战争、巴以战争、印巴战争,这个世界充斥着不合理的死亡。轰炸之后城市只剩一片焦土,平民只是日常地生活中,然后数万人死亡,千万人流离失所。
加缪在《鼠疫》里描绘了这种死亡的荒谬,一群群黑鼠走到阳光底下,在光天化日下死去。突然,人们开始发病,开始窒息,开始长出巨大的囊肿,开始痛苦挣扎,随后死去。城市戒严,街道戒严,尸体被堆放在一起焚烧:一个坑洞烧男性,一个坑洞烧女性。人作为人的尊严与自由被剥夺了,所有人在死亡面前平等。
他们早已看到过一些孩子的死去,因为,好几个月以来,恐怖的鼠疫是从来都不选择祸害的对象的。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早晨这样,一分钟接着一分钟地苦苦忍受着痛苦。这些纯洁无辜的孩子受到的痛苦折磨,它不是什么别的,就是一种令人愤慨的耻辱。但是,在此之前,他们还仅仅只是抽象地感到愤慨,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如此长时间地、面对面地注视过一个无辜儿童的垂死挣扎。
这时,孩子的胃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住了,身子又弓了起来,嘴里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好几秒钟里,他的身体就这样凹成了弓形,全身一阵阵地战栗着,仿佛他那脆弱的骨架被鼠疫的狂风刮得根本就挺不直,被高热持续不断的发作折腾得已然断裂。一阵风暴过后,他稍稍松弛了一点,热度似乎也退去了,把他遗弃在某种潮湿而又发臭的滩岸上,任由他在那里苟延残喘,让临时的歇息慢慢地变成永久的长眠。当灼烧的浪潮第三次向他袭来,稍稍把他掀动时,这孩子紧紧地蜷曲成一团,退缩到床角,高热的火焰烧灼着他,他突然发狂似的晃起了脑袋,蹬掉了被子。大颗的眼泪从烧得又红又肿的眼皮底下涌出,开始从他铅灰色的脸上流下。一阵发作之后,疲竭的孩子又蜷缩成一团,短短四十八小时里,他的两腿早已瘦骨嶙峋,两条胳膊上也没有了肉,如干柴一般,在凌乱不堪的床上,摆出了一个像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怪诞姿势。
那孩子还在竭尽全力地挣扎。里厄不时地伸手,去把孩子的脉搏,他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那只是为了让他自己从束手无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一闭上眼睛就能感到,孩子的垂死挣扎跟他自己热血的流动已经浑然交织在了一起。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已然不分彼此,就尝试着尽自己尚未消耗的全部力量去支持孩子。但是,他们两颗心的跳动只会合了一分钟,随后就不一致了,孩子挣开他的手,他的努力彻底落空了。
加缪在《鼠疫》这本书中想表达的都在这一段里,这本书的主题:挣扎,或者说是反抗。面对巨大的灾难,有道德见识的人会觉醒,采用各种各种的方式做反抗。主角里厄大夫组织卫生防疫小队,坚决要和疫情做斗争。他看着一个个病人死在面前,作为医生,他清楚地知道死亡是不可战胜的,所有人在自然规律的终点遇见的都是死神。然而他的态度却是继续做好本职,决不投降,抗争是他生命的本色。
另一个角色,从巴黎而来的记者朗贝尔。他不属于这座疫情城市,一心想逃离出去。官方渠道走不通,那就尝试偷渡。在等待偷渡期间,他暂时协助里厄大夫的防疫小队,逐渐感悟到生命的反抗精神,而不是逃避逃走。最后他放弃了偷渡离开,全身心投入他的抗争工作。
和他相对的是书里的神父,他全身心信仰天主,他不像这几位反抗者那样痛苦,他始终是平和的。信仰使人感到安宁,因信仰者没有自我,他将全身心献给神灵。因此在他被怀疑染上鼠疫后,他坚持不去看病。他说“对天主的爱是一种艰苦的爱。它得假设有一种对自身的彻底抛弃,对个人安全的无视,只有这种爱才能使死亡成为必要。这就是信仰,它在世人的眼中很残忍,而在天主的眼中却具有决定意义,我们必须向它逐步靠拢。这样的一个极端形象,我们必须努力向它看齐。在这一高峰上,一切都将混成一体,互相平等,真理将从表面的不公之中涌出。”
然而这种平和,并不是加缪想要表达的,加缪将自己的反抗和悲悯关怀都浓缩到里厄大夫的朋友,让·塔鲁身上。这位防疫小队最初的组织者,一位法官的儿子。他早年因旁观了一次死刑的惨状,从而认知到自己当初对现有规则的沉默,实际也是间接赞同了千万人的死亡,原来自己也是一个鼠疫患者。
“您从来没有看到过枪毙人的场景吧?肯定没有过,通常观看这样的场面是要经过邀请的,观众也都是事先选择好了的。结果呢,您也只能停留在书本上的描写中。一条布带,一根木桩,站在远处,几个兵士。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您可知道,行刑队就站在死囚犯身前的一米半处?您可知道,假如死囚犯向前走上两步,他的胸口就会碰上枪筒?您可知道,在这么短的距离内,行刑者会把枪弹都集中打在心脏的区域,所有人都集中起来,所有子弹都集中起来,他们会在囚犯的心口打出一个洞,足以伸进去一个拳头?不,您是不会知道这个的,因为这些都是细节,人们是不会去谈论的。
于是,我意识到,在以往漫长的岁月中,我一直就是个鼠疫病人,然而,与此同时,我还满以为自己是在跟鼠疫做着不懈的斗争呢。我得知,我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人的死,甚至,就在我赞同那些最终导致人走向死亡的行动与原则的同时,我就已经促成了这一死亡。其他人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尴尬,或者,至少,他们从来就没有主动地谈起过这些。而我,每每想到这一点,就会感到喉咙发紧。我跟他们在一起,却感到孤单。有时候,当我表达我的那些顾虑时,他们就会对我说,必须好好想一想,究竟什么才是问题所在。他们经常给我灌输一些非常惊人的理由,好让我囫囵吞下我实在难以下咽的东西。那些鼠疫大病人,那些穿大红袍的人,同样也能找出很像模像样的理由来,而假如我同意接受由那些鼠疫小病人提出的不可抗拒的理由,接受他们所加的不可违反的约束,那么,我就不能够驳回那些大人物的理由和束缚。他们提请我注意,要证明那些穿红袍子的人有道理的好方法,就是让他们去判断死刑的权力。但是,我心里又想,人们一旦让了步,那可就止不住了,会一让到底。看起来,历史似乎也证实了我的想法有道理,今天,他们正是在比赛杀人。他们全都杀红了眼,而他们也不能不这样做。
“从此,我就没有转变过。很久以来,我就感到很羞愧,因为自己曾是个杀人者而羞愧得要死,哪怕那时候还只是远远地认同,哪怕还只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无法确保自身的一举一动会不会导致别人死去。是的我一直持续感到羞愧,我知道了这一点,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处在鼠疫之中,所以失去了内心的安宁。直到今天,我还在想方设法地寻求这一安宁,我试图理解他们所有人,不让自己成为任何人的死敌。我只知道,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一个鼠疫病人,就必须做该做的事,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有希望得到安宁,或者,在得不到安宁的情况下,也能心安理得地死去。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即便不能彻底地拯救他们,至少也还能让他们少受很多罪,有时候,甚至还能让他们得到一点点快乐。因此,我决定拒绝任何会导致人死去的事,无论是打发人死亡,还是判定让人死亡,而且,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无论是近还是远,无论是理由充足还是强词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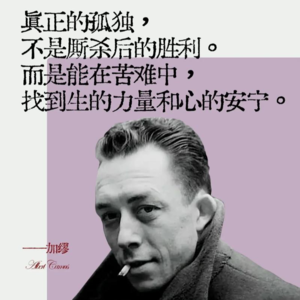


 70
70 0
0